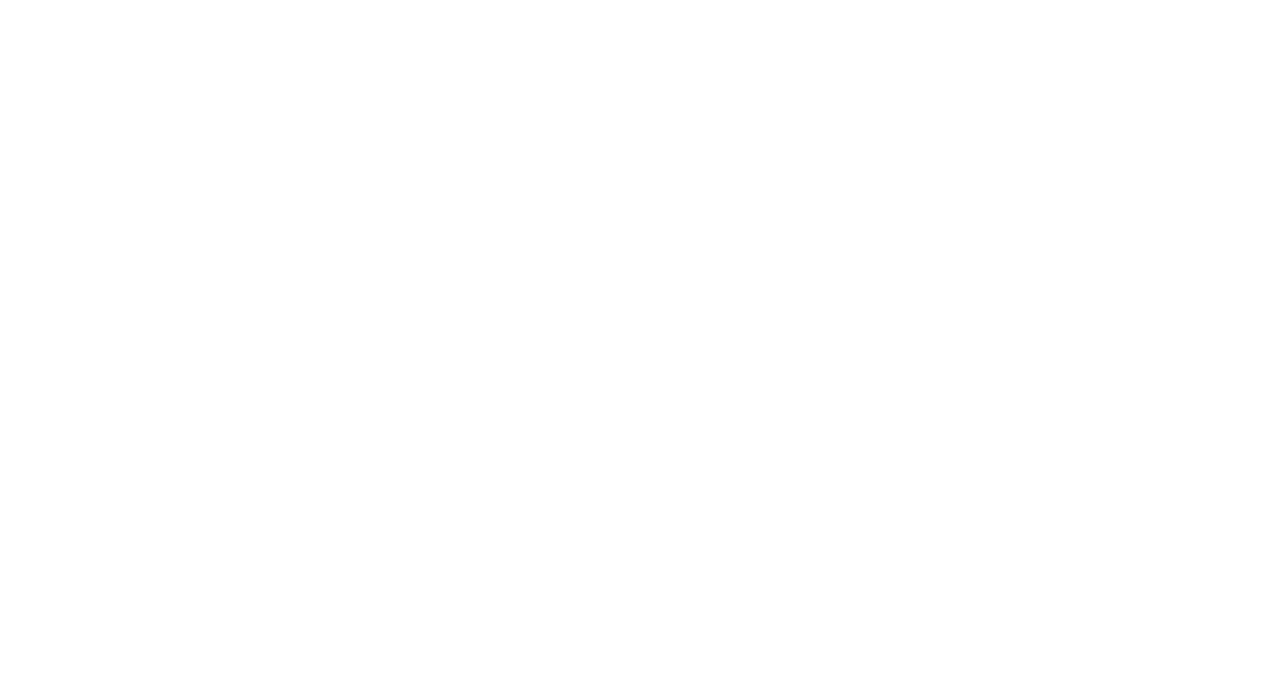essay
光的碎痕与沉默的丰饶:
——纪念菲利普·雅各泰百年诞辰
文 / 姜丹丹(Dandan Jiang)
一百年。一个世纪的刻度落在菲利普·雅各泰(Philippe Jaccottet,1925–2021)身上,仿佛一片轻盈的雪,在尚未触地前,已反复折射过日光的微光。2025年6月,我们纪念这位法语诗坛的清醒隐者、凝视微明的诗人思想家。雅各泰的百年,没有喧嚣的庆典,而是一封静默的邀约,邀请我们再次步入那片由“碎痕”“微光”“沉默”与“不确定”织就的丰饶之地。
雅各泰的诗与诗化文本(包括随笔、日记、艺术评论等)拒绝宏大叙事,却在尘埃与露珠中窥见永恒,探寻“在此时此刻真正的生活”的可能。
对我而言,翻译雅各泰从不是语符之间的简单转换,而是一次次寂静而谦卑的“趋近”(approche)。他以这种姿态趋近荷尔德林与里尔克,做那“渡船人”;也以此方式凝望莫兰迪静物画中如月光般的薄纱——终其一生,他都在执着于那不可言说的真实,追寻稍纵即逝的“在场”(présence)中潜伏的微光。
他的词语,是光的居所,同时也载着脆弱的质地。它们精准地捕捉光线的颤动、云影的流转、落叶的轨迹,却又谦卑地承认语言之于真实的“有限性”——这种有限并非终结,而正是诗意的起点。翻译他的诗,是用“心的耳朵”倾听低音吟唱的“小调”(minor music),在汉语的土壤中,重新培育“趋近”的伦理,练习对诗之低音的领会,如古代画师以笔传神,在细微之处显现神韵。
雅各泰的诗,如他的人生,是“减法”的艺术。他剥离修辞的繁复、抒情的高亢,乃至“诗人”的身份光环。他向往老子“为道日减”的境界,隐居于法国南部格里昂,在日常耕耘与沉思中,将生活简化至本质,留下最精粹的词语,如冬日里遒劲的枝桠,指向澄澈的天光。他的诗简约却隽永,如唐代绝句、日本俳句般凝练。在《播种期》(La Semaison)中他说:诗,是“一盏盏小灯笼,燃着另一种光的投影”。
他教我们练就“第三只耳朵”(la troisième oreille),去聆听微光中的奇迹:一朵花的开放即宇宙的隐喻,一阵风掠过麦田是时间的叹息,一次日升日落成了生死的仪式。深度并不在远方,而是在此刻,在气息微颤之间。
雅各泰书写可见之物(le visible),却总指向不可见(l’invisible)。雪花的坠落是轻盈的,也是沉重的,它可能藏着死亡的幽暗,也可能预示寒冬将尽的生机。即使在怀疑与悲伤中,他依然守护对“光”的执念。他笔下的光,从不耀眼,而是如东方鱼肚白般的黎明之光,是风中摇曳的烛火,是沉默边缘挣出的星火。那微光,是希望,是诗意的抵抗。
他在诗中写道:
“世界
石头的重量
思想的重量
梦想和山岗
没有同样的天平
我们还是住在另一个世界
也许在两者之间”
他是一位走在“边缘”的诗人——游走于可说与不可说之间,确信与怀疑之间,在生与死的缝隙中刻下诗行。他拒绝教条,始终保有怀疑与惊奇(étonnement)的目光。他教我们,在不确定中依然种下光明的种子,以深情凝视每一个寻常瞬间。正如他写下的:
“一切颜色,一切生命 / 在目光停驻处萌生 / 这个世界 / 只是一场看不见的大火的山脊。”
如小林一茶所言:“在地狱的屋脊上,看花。”
作为《雅各泰1946–1967》诗集的中文译者,我感受到,要迎接他的诗作与诗意伦理,需要调动汉语自身那尊“空灵”“淡远”“意在言外”的古老诗学传统。老子说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,王维写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,正如雅各泰在沉默中屏息聆听宇宙回响。这种跨语际的共振,是诗意本身的邀请。
纪念雅各泰,最好的方式是重读他的诗篇(如《具象缺席的风景》《播种期》等),用他的方式凝视草叶上的露珠、倾听风的絮语与沉默的共鸣。也是学习他对词语的克制——言之未尽,是因为“言不尽意”;学会在“少”中藏“多”,在“轻”中见“重”。
雅各泰的诗歌,给出了追求本真生存的伦理:放慢脚步,卸下心灵盔甲,以赤子之心,触摸世界的微妙脉搏。即使面对失落与晦暗(l’obscurité),也能——也必须——在碎痕中辨识光的形状,在沉默中开垦意义的沃土。
愿这束来自格里昂村庄的“微光”,穿越语言的疆界,照亮世界各地读者的内心角落,唤起我们对自然、词语、与具体世界的深沉敬意。雅各泰的诗,是全人类心灵的晨光,是旅途中人们口中的那一杯清泉。
雅各泰的诗与诗化文本(包括随笔、日记、艺术评论等)拒绝宏大叙事,却在尘埃与露珠中窥见永恒,探寻“在此时此刻真正的生活”的可能。
对我而言,翻译雅各泰从不是语符之间的简单转换,而是一次次寂静而谦卑的“趋近”(approche)。他以这种姿态趋近荷尔德林与里尔克,做那“渡船人”;也以此方式凝望莫兰迪静物画中如月光般的薄纱——终其一生,他都在执着于那不可言说的真实,追寻稍纵即逝的“在场”(présence)中潜伏的微光。
他的词语,是光的居所,同时也载着脆弱的质地。它们精准地捕捉光线的颤动、云影的流转、落叶的轨迹,却又谦卑地承认语言之于真实的“有限性”——这种有限并非终结,而正是诗意的起点。翻译他的诗,是用“心的耳朵”倾听低音吟唱的“小调”(minor music),在汉语的土壤中,重新培育“趋近”的伦理,练习对诗之低音的领会,如古代画师以笔传神,在细微之处显现神韵。
雅各泰的诗,如他的人生,是“减法”的艺术。他剥离修辞的繁复、抒情的高亢,乃至“诗人”的身份光环。他向往老子“为道日减”的境界,隐居于法国南部格里昂,在日常耕耘与沉思中,将生活简化至本质,留下最精粹的词语,如冬日里遒劲的枝桠,指向澄澈的天光。他的诗简约却隽永,如唐代绝句、日本俳句般凝练。在《播种期》(La Semaison)中他说:诗,是“一盏盏小灯笼,燃着另一种光的投影”。
他教我们练就“第三只耳朵”(la troisième oreille),去聆听微光中的奇迹:一朵花的开放即宇宙的隐喻,一阵风掠过麦田是时间的叹息,一次日升日落成了生死的仪式。深度并不在远方,而是在此刻,在气息微颤之间。
雅各泰书写可见之物(le visible),却总指向不可见(l’invisible)。雪花的坠落是轻盈的,也是沉重的,它可能藏着死亡的幽暗,也可能预示寒冬将尽的生机。即使在怀疑与悲伤中,他依然守护对“光”的执念。他笔下的光,从不耀眼,而是如东方鱼肚白般的黎明之光,是风中摇曳的烛火,是沉默边缘挣出的星火。那微光,是希望,是诗意的抵抗。
他在诗中写道:
“世界
石头的重量
思想的重量
梦想和山岗
没有同样的天平
我们还是住在另一个世界
也许在两者之间”
他是一位走在“边缘”的诗人——游走于可说与不可说之间,确信与怀疑之间,在生与死的缝隙中刻下诗行。他拒绝教条,始终保有怀疑与惊奇(étonnement)的目光。他教我们,在不确定中依然种下光明的种子,以深情凝视每一个寻常瞬间。正如他写下的:
“一切颜色,一切生命 / 在目光停驻处萌生 / 这个世界 / 只是一场看不见的大火的山脊。”
如小林一茶所言:“在地狱的屋脊上,看花。”
作为《雅各泰1946–1967》诗集的中文译者,我感受到,要迎接他的诗作与诗意伦理,需要调动汉语自身那尊“空灵”“淡远”“意在言外”的古老诗学传统。老子说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,王维写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,正如雅各泰在沉默中屏息聆听宇宙回响。这种跨语际的共振,是诗意本身的邀请。
纪念雅各泰,最好的方式是重读他的诗篇(如《具象缺席的风景》《播种期》等),用他的方式凝视草叶上的露珠、倾听风的絮语与沉默的共鸣。也是学习他对词语的克制——言之未尽,是因为“言不尽意”;学会在“少”中藏“多”,在“轻”中见“重”。
雅各泰的诗歌,给出了追求本真生存的伦理:放慢脚步,卸下心灵盔甲,以赤子之心,触摸世界的微妙脉搏。即使面对失落与晦暗(l’obscurité),也能——也必须——在碎痕中辨识光的形状,在沉默中开垦意义的沃土。
愿这束来自格里昂村庄的“微光”,穿越语言的疆界,照亮世界各地读者的内心角落,唤起我们对自然、词语、与具体世界的深沉敬意。雅各泰的诗,是全人类心灵的晨光,是旅途中人们口中的那一杯清泉。
Читать 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– «Свет в осколках и богатство в безмолвии»